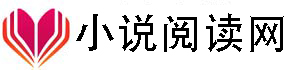20-30(16/33)
头走了。等老猎户的背影隐没在山林里,几个孩子才敢上前去拿。
铁打的箭头穿破了兔子的后脊梁,血腥气又浓又厚,也不知道是谁先说了一句:“他咋长得这吓人,和个伥鬼似的。”
那声音又低又轻,带着轻蔑和鄙夷,在场的孩子全都听见了,一霎间,都捂住嘴不讲话。
可沉默也不过片刻,有人小声附和:“就是说……那脸上全是疤瘌,瞧着可恶心人。”
“像个老倭瓜。”
“明明是癞蛤蟆。”
“哈哈哈是生了癞疮!”
嘲讽声四起,笑声轻狂,裹挟着没有缘由的恶意。
……
郑虎眼睛通红,他吸了吸鼻子,哽咽道:“我、我就不叫他们这样说,我说在背后讲人坏话,不是君子该干的事儿,‘仁、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人’。”
边上吉婶怔忪,郑虎嘴里的这一套套,她从来没听过,也不多明白,她咽了口唾沫:“这、这说的啥意思啊?”
郑虎没应声,只抽泣着继续道:“他们就都骂我,说我懂个狗屁,说我屁股上也长癞子,才向着人家说话。”
“我、我气不过,我就说这些都是川哥教我的。”
“川哥还同我讲‘爱人者,人、人恒爱之,敬、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
“他们说川哥干啥要教你,人家又不是你先生,净往自己脸上贴金。”
“我、我呜哇……”郑虎咧嘴哭起来,“我扯谎了,我说你就是我先生,川哥……我呜呜哇……我扯谎了!”
郑虎像是受了天大的打击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但这小子硬气,就是难受成这样,还是咬着嘴硬挺着,可半咧开的嘴角边呼哧漏风,哭声止都止不住。
沈柳瞧着心疼,忙走到虎小子跟前,撸长袖子给他擦眼泪。
桌案对面的顾昀川看着俩人,没有说话,那日晌午沈柳和顾知禧要做饭,他便帮忙看了会儿郑虎,也不过是临时起意找了本书,随口教了一两句,这小子不识字,念得磕磕绊绊的,却不成想竟全都记住了,还记到了心里。
他眉心紧蹙,指尖摩挲着骨节,像是在想些什么。
好一会儿,郑虎终于平复了下来,他从沈柳袖子边慢慢抬起头,哑声道:“多谢小柳哥,我哭好了。”
沈柳瞧着郑虎一本正经的小脸儿,轻点了点头,收起袖子走回了顾昀川身边。
郑虎坐坐正,呼出口气,等着挨说。
顾昀川看了他良久,没有责骂,只缓声道:“郑虎,你知道吉婶为什么要打你吗?”
郑虎咬了咬嘴唇:“我不该随便显摆,还扯谎。”
“这是其一。”顾昀川看着这个七岁的少年,用和成年人的方式同他交谈,“其二,你说我是你先生,被别人听了去,便想着我既然肯做你的先生,自然也可以做别人的先生。”
“他们提着束脩以礼相逼,我若驳回去就是伸手打笑脸人、不给面子,所以本来与我不相干的事,因为你的这些话,将我牵扯进来,平白挨人责骂,你阿娘觉得对不住我,因此才这么生气。”
郑虎听明白了,自椅子里站起身,态度很是端正地道:“昀川哥,对不起。”又转头看去吉婶,“阿娘,我知道错了。”
看着虎小子,顾昀川眼里有笑意,他摆手让人坐下,继续道:“但回到这件事本身,我觉得你没有做错。君子坦荡,不以貌取人,唯论德行,你做得很好。”
话音落地,郑虎耷拉的双眼倏然睁圆了,他被同行人嘲讽,被阿娘打骂,可川哥却说他做得很好。